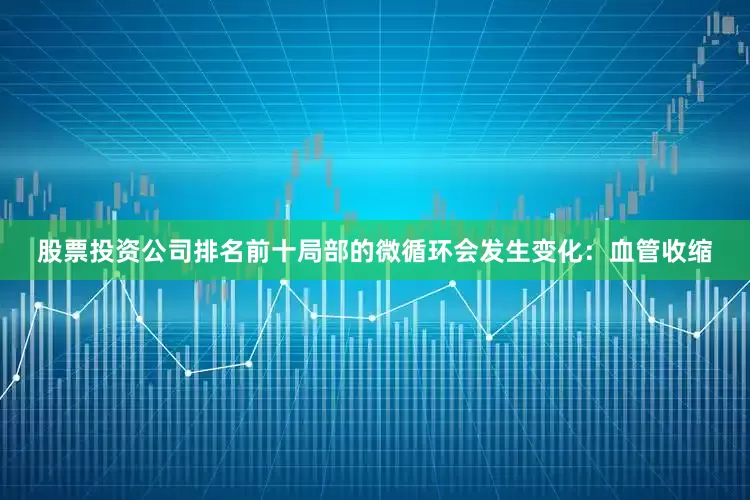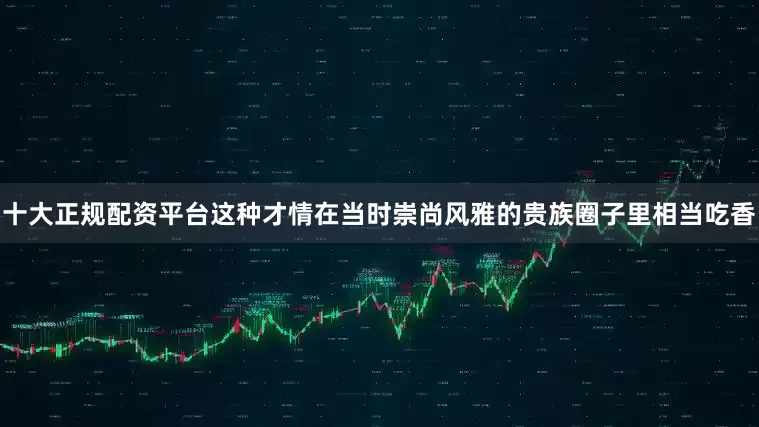
提起唐朝的张昌宗,很多人第一反应是"武则天男宠"的标签。但这位被称为"莲花六郎"的美男子,能在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绝不仅仅靠颜值。根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张昌宗出身官宦世家,父亲张希臧当过雍州司户,哥哥张易之更是武则天时期的红人。这样的家庭背景,注定他不可能只是个"花瓶"。
公元697年,太平公主把张昌宗推荐给母亲武则天时,特意强调他"材艺过人"。当时的史料记载,他不仅精通音律,能即兴创作乐曲,还写得一手好字。武则天晚年常在宫中举办文艺沙龙,张昌宗总能用琵琶弹奏新曲,或是当场赋诗,这种才情在当时崇尚风雅的贵族圈子里相当吃香。
但真正让历史记住他的,是那段充满争议的"母女共侍"传闻。太平公主先与张昌宗有私情,后又将他献给武则天,这种关系放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,但在唐代却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。当时贵族阶层盛行"进奉面首",即女性贵族之间互相赠送俊美男子作为礼物,这背后既有权力博弈,也是当时相对开放的性别观念使然。
展开剩余73%母女关系的特殊纽带
要理解张昌宗为何能周旋于武则天母女之间,得先看清太平公主与母亲的复杂关系。作为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,太平公主从小目睹母亲从皇后变成女皇的全过程,她既是母亲政治野心的见证者,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史书记载她"多权略,类武则天",这种相似的强势性格,让母女二人既有亲密无间的合作,也有暗流涌动的较量。
公元696年,太平公主的第二任丈夫武攸暨病逝,她开始效仿母亲公开蓄养男宠。把张昌宗献给武则天,表面看是女儿讨母亲欢心,实则暗含政治算计。通过这个"自己人",太平公主既能掌握母亲的生活动态,又能在武则天面前维持孝女形象。而武则天接受这份"礼物",既是对女儿示好,也是向朝臣展示自己依然大权在握,连亲生女儿都要争相讨好。
张昌宗在这对母女之间扮演着微妙角色。有野史记载,他侍奉武则天时总穿着太平公主赠送的熏香衣物,武则天闻到女儿常用的香料味,反而觉得更亲切。这种细节虽未必可信,但反映出当时宫廷人际关系的特殊性,在权力与亲情交织的深宫里,男女私情往往成为政治博弈的延伸。
美男子背后的政治筹码
随着时间推移,张昌宗兄弟的权力触角逐渐伸向朝堂。698年,张昌宗被任命为云麾将军,哥哥张易之更是官至麟台监,掌管国家典籍。他们利用武则天晚年多病的特点,开始干预朝政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二张经常"代则天批阅奏章",甚至发展到"百官奏事,必先过二张"的地步。
他们的崛起引发传统门阀的强烈不满。宰相魏元忠曾当庭指控,"昌宗不过陛下家奴,何得预政事!"结果反被贬官。更耐人寻味的是,太平公主此时态度发生微妙转变。她开始暗中联络李唐宗室,与昔日"进献"的张昌宗保持距离。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,在权力游戏中,男宠终究只是可弃的棋子。
神龙政变真实角色
705年的神龙政变成为张昌宗命运的转折点。传统史书将他描绘成祸国殃民的奸佞,但近年出土的《张说墓志》却透露新线索,政变前夜,张昌宗曾向武则天预警有人谋反,但被病中的女皇忽视。这说明他并非完全不知死活地专权跋扈。
政变当日,宰相张柬之率羽林军冲入宫中时,张昌宗兄弟正在长生殿侍疾。据《大唐新语》记载,他们临死前还试图用身体保护武则天。这种忠犬般的表现,与其说是出于爱情,不如说是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力完全依附于女皇。
被妖魔化的历史形象
后世对张昌宗的评价充满矛盾。宋代《太平广记》将他丑化为"狐媚惑主"的典型,但唐代诗人宋之问(曾依附二张)的诗作中,他却是个"风度翩翩佳公子"。这种形象分裂,本质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统治者及其宠臣的刻意抹黑。
现代史学家提出新视角,张昌宗现象是武则天晚年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。女皇需要既听话又有才干的近臣来制衡官僚集团,而寒门出身的美男子恰是最佳人选。他们如同精致的政治工具,用青春和才华换取短暂辉煌,最终成为权力更替的祭品。
发布于:江西省配资实力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