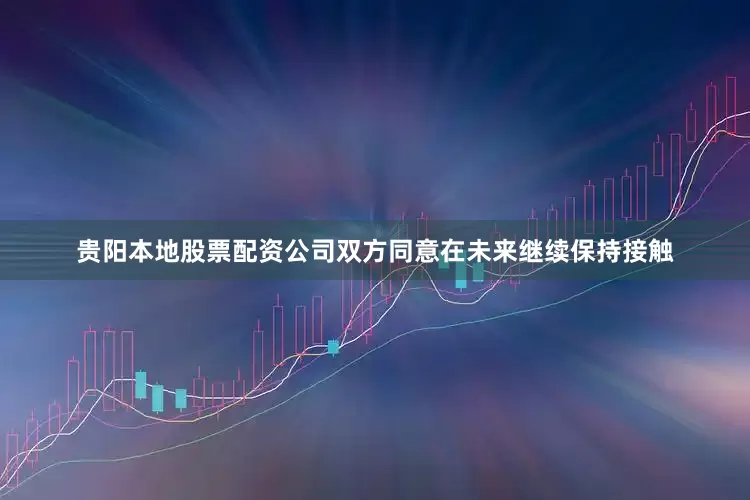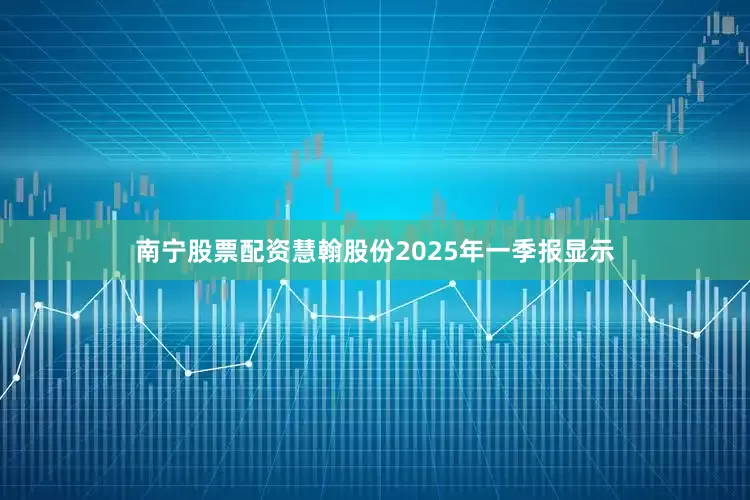古代史研读:封建统治下,新罗政局的衰弱与紊乱
七世纪中叶,朝鲜半岛进入了历史上的“统一新罗时代”(676-892),这一时期标志着朝鲜半岛从长期分裂走向了整合与稳定。统一新罗时代不仅是朝鲜民族文化与性格初步成形的关键时期,也成为推动古代东北亚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。统一新罗的建立,实现了朝鲜半岛统一三国的夙愿,奠定了新罗武烈王朝的统治基础。然而,自九世纪起,新罗政权内在的政治弊病愈加严重,社会矛盾不断加剧,无法调和的阶级利益使得新罗的封建统治逐步走向崩溃。
新罗一统三韩的壮丽景象虽然为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但随着新罗政治体系的逐渐腐化,国内的王位争夺与社会动荡频频发生。尤其是在惠恭王十六年(780)的春天,新罗王庭爆发了剧烈的内乱,惠恭王被乱兵所弑。金良相,时任上大等,继位成为新罗的第37代国王——宣德王。值得一提的是,金良相为奈勿王十世孙,这一王位交替不仅标志着新罗武烈王系的衰落,也为奈勿王系的继承开辟了道路。
新罗进入下代,特别是从九世纪初到真圣女王继位前,王位争夺与骨品制瓦解相继爆发,进一步加速了新罗政治体制的衰弱与僵化。这段时期,土地所有制的畸形发展,对新罗的经济基础构成了巨大冲击,最终导致封建统治的崩塌。
展开剩余81%这一时期的新罗政局,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政治纷争。新罗中代末期,内外局势相对平稳,这一相对安逸的环境却滋生了统治阶层的功利化和庸俗化现象。进入新罗下代,随着王位争夺与贵族叛乱的愈演愈烈,九世纪末的新罗政局几乎是被“王位争夺”与“贵族叛乱”所主宰。
其中,五次王位争夺战尤为突出,其余十二场叛乱最终被王庭平定。尽管现今无法确认其他叛乱是否以王位为目标展开,但我们可以明确知道,从宣德王到定康王的107年间,新罗爆发了五次王位争夺战,期间更是导致了三位国王的惨死。这些政治动荡不仅频率高,而且规模庞大,远超前代与中代,造成了新罗下代政权的严重动荡。
从人物关系的角度分析,王位争夺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第一类是武烈王系与奈勿王系的派系斗争。金敬信虽然成功夺位,但他并未彻底清除武烈王系,而是对其保持了一定的重视,然而这并未能彻底解决双方的矛盾。第二类则是奈勿王系继承体制失控,导致王位继承内乱。由于这些纷争的核心人物多为元圣王的直系后代,因此这些争斗可视为元圣王系内部的权力斗争。
新罗下代的王位纷争,不仅仅是关于王权的争夺,更多的是统治阶层内的权力博弈。尤其是上大等与侍中之间的冲突,显示了新罗“相权坐大”的现象。上大等是新罗的最高官职,掌管着政务的决策权,而侍中则是执事省的最高长官,负责制约和协调上大等与其他高层官员的权力。这种权力的结合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王权,导致了政局的紊乱和不稳定。
此外,八世纪中期至九世纪初期,新罗政坛的“伊飡”阶层逐渐膨胀,这些掌握实权的高官,尤其是伊飡职务的担任者,频繁参与谋反和政治斗争。伊飡职务在新罗十七个官职等级中排第二,仅限于真骨阶层担任,拥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权力。随着时间推移,伊飡阶层的频繁谋反反映出骨品制度的崩溃与政治秩序的瓦解。
新罗下代的政治环境呈现出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结构,但王位争夺与贵族叛乱的不断发生使得这一体系日益松动。文圣王继位之前,新罗的政治局势因王位争夺而战火不断,而文圣王继位后,贵族叛乱接连不断,政局动荡不安。长期的贵族叛乱迫使统治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刑罚措施,如“伏诛”、“缘坐”和“车裂”,以震慑叛乱分子。
新罗下代的频繁政乱迅速导致了中央集权的衰落,骨品制逐渐失去原本平衡政局的功能,封建统治岌岌可危。同时,基层的贫苦百姓和地方豪族的崛起,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。土地所有制的变动,特别是从国有到私有的转变,给新罗经济基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。三国时期,新罗实行食邑制与禄邑制并行的田制,后来在神文王九年(689年)废除禄邑制,推行了职田制与岁租制。但到了722年,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,新罗又重新推行了“丁田制”,这种制度与均田制相似,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保障统治者的利益。
丁田制虽保障了无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,却伴随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,农民的生活负担加重,实际上使得他们成为封建国家的附庸,保障了王室的财政收入。然而,随着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,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,丁田制下的农民纷纷破产,沦为贫农或奴隶,社会底层的压迫愈加严重。
新罗的土地制度经历了许多波折,最终形成了以丁田制与禄邑制结合的土地制度。禄邑制的重新启用标志着新罗的国王在面临贵族的压力时,选择了妥协。贵族不仅保留了封地的收租权,还掌握了私人军队,这使得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强大,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。最终,新罗的封建统治在贵族之间激烈的土地兼并竞争中渐渐崩溃,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,为九世纪末的农民起义及“后三国”局面的爆发埋下了伏笔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实力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